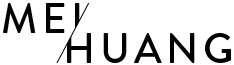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 新数码艺术与在线网络展示平台
发表于《当代美术家》2016年6月刊
伴随着微信、微博、推特与脸书等网络媒体的大众化普及,网络与生活的联系日渐紧密。网络也成为了年轻艺术家获取知识和交流的主要渠道。瑞驰索蒙 (Rhizome),一家小有名气的网络艺术网站总监对笔者说道:“现今网络简直就是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与网络和科技有关的艺术呢?”
新数码艺术的是运用当今时兴的数码科技制作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以视频影像和图片为主,内容用囊括了当下青年人中间流行的电脑科技、地下文化、波普和流行艺术;它主要的展示平台是网络。新数码艺术在理论意义上取代了传统画廊和策展人对与艺术家的必须性和约束性,并以网络为媒介创造了新型的在线展示平台。时下,新数码艺术这种风潮简直席卷了西方艺术界,就连众多顶尖艺术机构也开始跟随潮流,成立了新数码部门,更策划了很多重要的相关展览项目。例如在英国伦敦:策展人小汉斯 (Hans-Ulrich Obrist) 的蛇形画廊 (Serpentine Galleries) 成立了数码策展部,聘请了若干“数码策展人 (Digital Curator)”;英国基金 (British Council)会对新型在线艺术进行支持和投资订制;美国的新美术馆 (the New Museum) 策划了大型在线展览《抢先看:新在线艺术 (First Look: New Art Online)》项目,等等。事实证明,被称为“网络一代”的西方年轻艺术家目前的影响甚为巨大,卡罗/芬奇 (Carroll/Feltcher) 的合作总监 (co-director) 乔纳森·卡罗 (Jonathan Carroll) 认为:“我不能说新数码艺术是一种发明——它其实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新数码艺术标志了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文明。”他接着说,“这是我目前见到的最有趣的艺术运动之一,但作为在机构谋求发展的艺术工作者,这种艺术实际上是让我们很伤脑筋的:因为它完全打破了规则——我们作为艺术机构要怎样去展示网络在线艺术呢?”
数码艺术在西方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早在60年代,伦敦的ICA美术馆就举行了关于数码艺术的第一个展览《神经机械学巧合 (Cybernetic Serendipity) 》。这个拥有古怪名称的展览第一次在西方艺术史上展示了与科技和数码相关的艺术形式:例如,由当时还是三组书柜大小的“windows 1” 电脑绘制的尼克松人像;把音乐和文学语言通过电子极其转化成视觉语言;老电视机与艺术家的互动发明和各种由数码编程控制的装置等等。 《神经机械学巧合》向当时的世界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与机械科技的链接的世界。
无论赞同与否,现今的艺术世界是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与金钱,虽然听起来庸俗无比,却是推动艺术运动发展和艺术家进步的原始基础和动力。新数码艺术,这个听起来酷炫的艺术新名词在革新传统艺术规则、引领时代潮流和否定资本意义的同时,有着很多致命的局限性。
首先,新数码艺术靠什么来盈利?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靠点击率来生存的新数码艺术无疑在这个大社会背景下出于劣势——虽然尖端但不够主流。是否有收藏家愿意收藏购买?如果有,通过何种渠道?怎样体现其收藏价值?其次,在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所有权也是未知数;这确实对浏览艺术家作品网站的观者的道德水准要求过于偏高。另外,新数码艺术否定了艺术机构、策展人、交易人、拍卖行和中介等经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团队的价值。没有了这些艺术专业从业者支持,新数码艺术展览的品质和发展只是依靠艺术家自身的运作很难有基于理论和体系的发展,艺术家的创作环境也失去了健康保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新数码艺术普遍依赖于当今的科技发展并且基于流行元素,却鲜有认真严谨的调研和对艺术、文化和社会的深层次理解、反省和剖析。那么,这样的新潮艺术随着时间的流失,会保留下来吗?它们有实际价值吗?这是值得令人思考的。
2014年,在中国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举办了一场标题为《后网络艺术 (Post Internet Art)》的展览。这场由外籍策展人凯伦·阿契和岳鸿飞合办的巨型展览囊括了约40余位以三维酸(Aids-3D), 幸运PDF (Lucky PDF), GCC为首的被称之为“后网络艺术家”的作品。《后网络艺术》,顾名思义,是将许多曾经只在网络平台上展示的新数码艺术进行物化,以装置或者照片打印的形式在空间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展出艺术家中的许多人恰恰是曾经的新数码艺术(否定机构与策展人价值,提倡在线展示和艺术家绝对自由)的倡导者,这不禁让人觉得讽刺。
就拿“幸运PDF”组合来举例吧,这个由四位“网络一代”青年所组成的团队起初是新数码艺术的代表,并且成立了名叫“幸运PDF”的非盈利性网站——专门展出自己和其他网络艺术家的作品、音乐以及组织一些青年人的文化潮流活动。但后来他们的“非盈利性”网站慢慢掺杂了其他商业元素,例如与时尚品牌合作做新潮服装或者售卖印制自己作品的T恤;而在尤伦斯的展览中,幸运PDF干脆将自己在网络平台上展出的艺术作品转化成物化的装置和照片在展场进行展示。尽管他们自己宣称:“已经有很多新数码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转化成物理装置和摄影作品了。我们认为将数码和物理装置相互结合延伸这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但这却与幸运PDF之前的口号:“我们只创作概念,不生产艺术品。”的理念大相径庭。笔者虽然不否定对于这种新数码艺术的物化形式,但是却对这种现象表示质疑:新数码艺术在目前的发展中是否为了适应艺术市场已经渐渐脱离其创作的初衷?
暂且不论西方新数码艺术和在线网络展示平台的风潮与之后的发展是否对当代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可否定的是它的创新意义和对艺术知识的积极探索。但是就算在新数码艺术风潮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少有关于中国年轻艺术家加入这场艺术运动并且创作作品的新闻出现。中国北京尤伦斯那关于新网络艺术的近40名艺术家参与的展览却无一位来自中国本土便是一个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