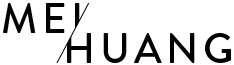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Just go, and you will arrive”
Published at Rhizomic Space,
Mongolia. 11/09/2021
作者:黄梅

“我感到我的肺部激荡进风、树木和人的气息。我想,这就是快乐所需的一切。”
— 《钟形罩》,西尔维娅·普拉斯
困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人们的活动逐渐始于清晨打开手机,点击社交或娱乐媒体,逐渐被各种信息碎片、社交焦虑、自我质疑和无休止的购买和欲望填满。哪里又发生了战争?疫情又在何处出现了?哪个偶像和爱豆又深陷丑闻?长久居于城市的我们已经逐渐忘记了如何去感受阳光、空气和青草的味道,以及如何用简单质朴的方式与自我和自然相处。
2021年由琴嘎发起的《一起游牧》是近期为数不多的吸引我细细看完每一件作品的大型项目,它以流动空间“造空间”的虚拟平台为载体,打破了时间和现实空间的限制,25位艺术家用诚意和作品细节谱写了一曲有关于自然与生命的交响乐章。在我看来,《一起游牧》向观者呈现了三个主要方向的反思:自然与当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艺术、自然与身体的链接;以及文化对与艺术家自我身份的映照。
我们是否别无选择?
两块同样的石头浸润在水中,一块是丛林和自然的笔墨,另一块由人类的肆意涂改和添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一块的痕迹会被毫不留情的抹去?蒙古国艺术家策仁皮勒·阿荣特古斯(Ariuntugs Tserenpil)的影像作品《无法命名的制造-21 (2021)》(Unnameable Manufature 21) 抛出了这个问题 。伴随着流水声,艺术家用做了虚化处理的手指在两块并列的石头上用水迹涂抹抽象的几何图案。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代表人类造物的石头随着水迹的干枯逐渐消失在漆黑的背景中,而象征着自然的岩石却留了下来,水滴在翠绿的森林背景中缓慢的汇聚成了代表生命力的河流。艺术家使用影像的视觉语言表达了他对于自然的无限眷恋和情感。如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减少对自然的伤害?我们是否除了此路之外别无选择?人类的造物究竟是否永恒的?这是阿荣特古斯的思考和疑问。
同样探讨生态破坏问题的还有孟和琪琪格·扎拉哈扎布(Munkhtsetseg Jalkhaajav)的作品《瞪羚的梦 (2020-21)》(Dream of a Gazelle) 。在扎拉哈扎布的创作下,瞪羚瘫软的躯干呈扭曲的姿态无力的吊挂着,并且本该奔跑的前蹄被替代成了人类的双手。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双手本该象征着创造,在这件作品中却暗喻了人类对其他生物的禁锢和虐杀。《瞪羚的梦》由视频、软雕塑和拼贴画组成,以小动物的梦境为叙事主线,从侧面讲述了瞪羚丧命于草场围栏的设立的人为悲剧故事。
有意思的是,全宝(Burenerdene)创作的行为/影像《礼物 (2019-10)》(Gift),则向观者诠释一种由游牧这个概念而衍生的自然和轮回的可能性。枯萎的干草映衬着矮山的萧瑟,影像中没有任何音乐,只有风声作为伴奏。全宝将聚集了对去世额吉(母亲)的思念和草原的热爱的、由传统奶质工艺制作的一颗等大的牛骨头颅放置于家乡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度草原上。这份源自艺术家的爱的礼物象征着一枚精神符号,正如世间万物一般,逐渐融入和消解在自然的包容和轮回之中。
这种自然轮回和循环的理念更像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层层递进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仅只是表现在艺术作品的创作,同样涉及了公共教育和社会实践层面。于伯公的项目《移动的学院 (2021)》(Mobile Academy) 以城市作为基点,以游牧的循环:自然—社区—城市—自然的行动方式为带领以儿童为主的学员去野外采风,学习自然的创造方式以及如何与土地相处。而刘商英的《家族树 (2021)》(The Family Tree) 则由一棵树的故事为起始点引深到自然对于中式家族观念的影响,以及在当下大规模城市化的语境之下农村居民的选择困境:是离开这片扎根的土地还是选择继续守望?
自然与当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无比复杂的,更多时候,当代人拘泥于自身眼前的烦恼和困境而选择无视或从未认真思考过自人与大自然的共存方式,从娱乐和消费中找寻短暂的满足和快乐。直到污染、全球气候变暖和病毒影响到自身生活时才真正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所在。处在“游牧”中的艺术家们似乎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文化、传统与血脉之间的联系,去除那片遮挡双眸的叶子,他们抛出的困惑和问题正是以自身经历和思考映射了当下与有关的社会议题。这是一种自发的选择,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重启身心灵的感受与链接
多年前在网络上发现的一张名为物理学霍金斯能量的图表让我印象深刻,根据该图显示,生命的能量和情绪联系着身体的触觉、听觉、味觉和视觉等各种感官,而感官和情绪的能量的物理粒子震动频率使得我们的肉身以及世界呈现目前的样子。的确,感官和身体是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媒介,也是我们与自然的最直接链接。它们如此强烈,使得外在的经历和觉知逐渐变成我们自身经验,塑造了自我,乃至本我的一部分。在《一起游牧》中,混合了触觉、听觉、嗅觉和视觉的作品无疑感官给了观者的肉身感官一种最直白和强烈的冲击。
东妮尔 (Nini Dongnier) 的《场域记录4: 每一动都是仪式 (2021)》(Field Record 4: Every Motion is a Ritual) 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身为舞者的东妮尔并没有像观者预想的那样在影像中翩翩起舞,反之,她将用纯羊毛染色制作的巨型草球置于野外,使其伴着风声和牛羊的吟唱声随风佛动。高清影像让“草球”中的每一根毛发的机理跃然屏幕之上,风柔情的抚过,糯软,滑顺,轻盈的像极了用精神的触手抚摸毛皮和草地的触感。这是自然界的纯净的美与舞蹈,舞者东妮尔更像是一位旁观者,向观者传达她对于自然的领悟。“放松,等风来,”这是一句多美的哲学。
艺术家那林呼 (Nalinhu)、盛洁和琴嘎 (Chyanga/Qin Ga) 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与听觉链接。在《寻找扎格斯台淖尔I、II (2020)》(In the Quest of Jigasiai Lake I/II) 中,那林呼用收集和采录的方式将第一部收录的扎格斯台淖尔(湖)的风、水等自然声音和第二部在他工作室的人工机器合成的电子声音做出了对比。虽然演绎源自同一个曲调,前者在野外的影像是对于记忆中家乡和自然的致敬,而后者闪着蓝紫光线的酷酷的钢铁音乐装置是艺术家对于机械化时代的反思。不同于取之于自然的声音,低沉的,持续不断的低音琴弦声充斥着盛洁《罗布荒原上的狂欢 (2020)》(The Carnival on the Lop Nor)的整篇乐章,如黑暗中的千军万马的挺近,间接性的刺耳的婉转停顿又默念着曲折与苍凉,像极了寒冬午夜时分月下斑驳的草原景色,又似老者在讲述和回顾无奈却又不得不接受的那些命运中悲欢离合的故事。琴嘎的影像《围栏剧场 (2019-21)》(Fenced Theater) 则是一部蕴含了社会实验的声音雕塑。艺术家与男女老少牧民们或并排而站或席地而坐,自然随意的聊着关于对于牧区草场围栏的看法。大风呼啸着,断断续续的盖过了人们说话的声音,所有的语言好像被自然冲散了,又缓缓再次聚集起来,自然好像也加入了人类的讨论;孩子对话中跳跃玩耍,动物叫声的插入;到最后,观点和讨论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围绕着塑造和刻画着一场有关于草场围栏的情景剧集。
恩和保力道· 陶德弥德希热沃 (Enkhbold Togmidshiirev) 的作品总与气味相关,这次也不例外。在影像《蓝色的觉醒 (2020)》(Blue Awakening)中,迎着燃烧马粪的呛鼻的烟熏气味,他喝下烈酒,用双肩扛着蒙古包的木质框架,披散着长发,赤着双脚,从葱郁碧绿的草原出发,面容肃穆的一步步走向那堆漆黑的灰烬。
仓浩日乐·额尔德尼巴雅尔 (Jantsankhorol Erdenebayar) 的装置则是取了视觉“巧”劲的。他的灵感源于北美地区汽车后视镜里的一句话“镜子里物体比你看到的更近 (Object in Mirror Are Closer Than They Appear)”,这句话也成为了他作品的名字。在艺术家的眼中,每个后视镜出场所带的行车安全提醒经过仔细思考后却像是一句一语双关的哲学警示。额尔德尼巴雅尔的镜子被镶嵌兽角与做旧木材的包裹中,观者被邀请看向镜子中的自己。你看到的是真实的自己吗?还是自己心理深处的一种投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于历史和自我身份认同的观照。
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们因何活在这个世界?
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终极使命之一便是要找寻真正的自我。我们看似为独立的个体,可以依照自己的选择而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我们特定的基因遗传,我们出生、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肤色,我们出生时围绕于我们的文化、家庭宗教信仰,我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的母语,虽然是偶然的,却也是难以改变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分析道,由于世界与世界间的往来逐渐频繁,人们对于其他文化之间的认识也慢慢加深,导致宗教信仰时代逐渐过去了,但是人的受苦却并未消失。上帝死了,天堂解体,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既然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么如何找出存在的意义,延续生命的形式?因而,“这个世界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今天,带着当代的智识,回归自然,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仪式是一种自我找寻和认同的方式。艺术家乌云额尔德尼 (Oyunerdene) 在装置作品《我的空间 (2021)》(My Space) 中,将传统的蒙古画技艺作了当代性的拓展和延伸,历时一个月,她在白色的丝绢上细细用笔墨勾勒描绘了与自己印象中有关的游牧生活的一切,并把布块置于她老家牧场的马匹身上。白布随风飘动,那些画中的人物和景物也似活了般运动起来。强烈的阳光将草地和周边蒙古包的景色反射在白布上,双重画面的叠加犹如风撩起了鳞波湖面中的水月镜花,眩目异常。音乐家蒙柯卓兰 (Zulan)的《轻柔的风 (2021)》(The Wind is Gentle)中对于蒙古长调与电音的运用和藏族艺术家边巴 (Pen Pa)的《窗 (2020)》(Window) 里对藏族传统民居里窗户的拓印和以此为基础的画作都可以展现艺术家们以当代视角对于其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取和再创造。
刘成瑞的《双格达 (2013-21)》(Shuanggeda) 则是个更加有趣的例子。艺术家认为“ ‘血统’和出处已不是将自己归类于某一个群体,而是作为个体在当代的普遍性中延展出另一个完整丰富的想象空间。” 带有隐喻意义的火圈,或现代的或民族的服饰,仪式化的行为和缓慢的长镜头贯穿他整个三部分的作品,刘成瑞对于自己作为生活在城市的游牧民族后裔的身份和被汉族姓名遮蔽的少数民族血统不断的尝试着进行着回应。
当然,这也引申出了当下激烈的讨论:当代艺术是否不需要呈现民族性和特殊性?对于民族的符号和自身传统文化的强调是否构成了“异域风情”或者是将作品限定到了一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还可以把这些问题放大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否不需要呈现中国性?是不是运用了民族、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和符号便疑似是一种“东方主义”,没有站在“全球的学术背景”下与世界平行?我们假设这些疑问都是肯定的,那么,那些完全洗去自身文化背景,全盘接受其他文化作为主导的艺术家们,难道不是文化同质化的牺牲者?那也是一种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很欣赏艺术家乌日根 (Urgen) 在《来自地球的声音 (2020-21)》(Voice from the Earth) 中的宣言 (manifesto),他很好的回答了上述这些问题:“艺术是自己选择的行为,我的艺术服从自己的内心,并跟着感觉探索历史、时间、空间和现实意义的生成中。作品是我进入社会和文化对话的媒介,同时也是我在处理身份认同或历史背景时,诠释其差异的过程。艺术是通过转换形式和空间并借助媒介来实现作品对现实的介入。所以,艺术家对世界的思考是投射这个世界的裂痕,而不是当下的和解。”
后记
在2020年,我因即将在今年秋冬季出版的新书“Xina avui: minories, cultura i societat” (《今日中国:少数群体,文化与社会》) 对琴嘎进行采访时,他曾对我提到家里老者经常对他说的一句源自成吉思汗的非常有启发的话:“不要因为路远而踌躇,只要去,就必到达”。对于内蒙古和蒙古国当代艺术的了解和研究,于我而言更像是打开了一扇无比有乐趣和内容丰富的大门。2020-21“一起游牧”今年八月份的落幕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具有更多潜力的开始。愿“游牧”繁荣继续,远走在打破文化壁垒和偏见的路上,创造未来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