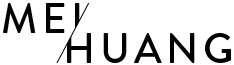二〇一七
发表于《艺术商业》2018年2月刊
转眼2017年已入尾声,这一年似乎过的特别快,时间在大多数人未曾察觉的刹那就飞速流逝了。艺术世界倒不曾改变,今年尤其热闹非凡。大到国际级别的光线展览、巴塞尔的华丽盛会,小到地区级的双年展换着地方不停开幕,就算是较为偏僻的旅游乡镇也会被名流包围,门庭若市。大家冲着市场目标前行,应酬不断,酒桌前觥筹交错,前景似是一片大好。
今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是当我从某个旅游乡镇艺术展场的华丽盛会走出来。穿过有保安守护的、层层检查的铁栅栏大门,迎面而见的是一排卷闸门紧闭的、已经关门歇业多时商铺,和空无一人的斑驳街道。展览除了衣着讲究、妆容精致的艺术和媒体同行外,看不到任何本地居民的影子。那个时候我便问自己,艺术究竟为何物?这些由房产商赞助的大型艺术展览除去明显的经济目的之外究竟是否会给本地带来艺术教育和发展?转头问了一位同行的艺术家,他指着那些正在铺草皮的农民工说:“你看他们,有了这个展览,他们可以多铺草皮赚钱啊。”
艺术的确是主要属于上层以及中上层经济构建的游戏,毋庸置疑。但我认为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艺术之所以被称之于伟大,是因为它可以超越阶级的构架,帮助人们了解自身、增进对世界的认知和反思这个时代。
纵观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及运动,从文艺复兴开始,到现代主义艺术革命,再到后现代主义艺术;无一不是打破和挑战了原有的阶级限制和局限性,剖析真实的社会现状,挑战自身。这也是艺术和艺术史令人感动和折服的原因。但是走在如今繁华的艺术盛宴中,却又是另一番感受。一幅幅完美的挑不出毛病却也不知道究竟好在哪里的作品,空洞和华丽并存;有的甚至一眼就知道其原本的“灵感”出处。很多人在华服倩笑和高脚香槟杯的折射出的五光十色的幻影中迷失了初衷。
翁贝托·埃可在其《开放的作品》中说道:“美学价值并不是同整个历史局势,同时代经济结构绝对没有关系的东西。艺术产生于历史联系中,它反映了这种联系,并推进这种联系的进展。”仅仅单纯的去批判当下的艺术现状,其实也是不完全公平的。时代于此,或融于规则、隐忍匍匐以待一日翻身坐上权利交椅;或是逆流而上,为人所不为,大多数人因违反常态而被惩戒、无人问津,屈从现实而消失于洪流之中。只有少数极其坚持执着的幸运者被伯乐挖掘。
或许这只是一篇乌托邦的年终总结。2017年是多事的一年,有很多东西都与以往不同了,或者说是更清晰或是模糊了。在福柯理论中,他认为阶级(权利机器)是不会反思自己的,它只会愈来愈固化,直到消灭人类的意志。世界格局也在急剧的变化着,从川普当选,欧盟保守极右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北韩的核武器威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又起,没有人会知道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并不期待有什么惊世作品的出现,只是希望在多年后回顾现在,在这一团和气和繁荣的背后,能够找出清醒的思想者和以反抗者的姿态呈现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