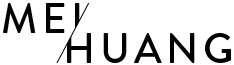采写/整理
黄梅
本文发表于《艺术权利榜100》2020年6月
策展人,批评家,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利用疫情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危机,但也是我们不得不创新的机会。我们会在网络平台上做一些事情,特别借以重新认识网络数字文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改变。我们需要如何去面对它?我觉得至少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不得不去这么做,先用之以作为一种过渡,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到正轨上去,但是这个能不能回得去大家也未曾得知。另外一种就是,在近二三十年,数字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在生成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激烈彻底的。我们一方面是顺应这种变化,一方面也用批评的方式来面对它,这很重要。很难有一种结论来定义网络数码平台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但它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阶段的一个讨论就是,网络和数码的技术对于各个领域的冲击:特别是关于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这样根本的问题。这种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去保持我们的批判性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具体来说,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去重新去重视中小型的艺术机构,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文化企业,的生态,并且找出各种支持的办法——虽然大家都不太明确如何去做,但是首先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去讨论。其实在经济界也是一样,除了几个大公司垄断的以外,其他的中小企业在过去20年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在新技术性的投资浪潮兴起时,出现了很多小企业(start-ups),但是它们的目的经常是作出一两个创新的产品,并马上把这些产品尽快转变为更大的市场价值,把它卖给大公司。这种主动接受大公司垄断的做法,就有点像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马上很想进入一个画廊,然后把作品价格尽量提高,把自己“卖给”一个大画廊,这种逻辑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够怪艺术家本身,因为艺术家也要生存。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颇为无奈。但是我觉的我们作为在大机构里工作的人,或者是艺术圈里负有一定层次的责任的人,我们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怎么去把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拿出来讨论,请大家一起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艺术世界逐渐变得封闭、单一化和民粹化是非常危险的。虽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然反应,有点类似于条件反射。要用包容的看法去理解这个事件,因为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但越有这种反应我们就越需要看清楚,实际上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我非常能够理解,当我们突然受到使得我们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的某一种外力的冲击,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要拒绝外来影响,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方式。我也相信有很多人讨论过新的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出现,特别是背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对它的操纵,这是非常危险的。从我们的艺术和文化领域来说,首先是要认清“全球化”给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哪些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更重要的区分不一样的“全球化”的“气候”:比如说1989年是冷战结束后非常重要的一年,两种冷战的体系对于人类的好坏可见一斑——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专制集权。同时不可避免的这也也有经济的问题,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对我们更有利。当然这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但这不是说全球化的愿景本来就是一个坏的东西。那么「这个愿景需要怎么去实施?」「各种不同愿景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它们引发出来的各种计划和措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去分析。比如说在艺术圈或文化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你在西班牙我在法国对谈,而不是在北京或者某一个地方。这证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那么这是好是坏?我想至少对于你我来说肯定是好的。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人——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但这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创造一种条件让大家能够自主地去选择非常重要:他们要在什么地方去生活?要怎么去生活? 这是最根本的。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叫「好的文化价值」,「好的生活价值」。这是一个难以一言定义的讨论,探讨会无休无止。从艺术方面来说,过去只有西方的当代艺术是最主要的,现在西方以外的当代艺术是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是得益于1989年开始的全球化,当然也可以追溯到100年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等等。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方式已经不是要把东西方加以黑白式的区分,而是加入了南方、北方各种坐标了。这些坐标有它实质上的意义,但是也有局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拷问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断地调整坐标的意义和它的运作方式。我们的信念需要坚定。虽然我们未必能说服很多人,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课题提出来。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了。不能给自己画一个舒适的区间,然后在里面自娱自乐。艺术和其在社会中的理解和角色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展览、评奖、批评等等,能够不断的去做坚持去做你坚信的事,给艺术圈某种信号,这是非常重要的。